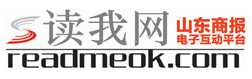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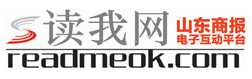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王君超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前者在于互通有无的包容性,后者在于既得利益的集权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向海而生,面海发展成为一种共识。如何理解海洋,理解大国博弈的本质,穿透海陆文明的冲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从而更敏锐地洞悉文明的来路与方向,是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兰伯特的著作《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一书带给读者的启迪与思考。
大陆国家和海权国家因其生产资料的来源和分配方式不同,决定了未来创造出的国家内涵将形态各异。《海洋与权力》在导言部分对两种政治生态模式进行了界定,它指出大陆列强的理想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海权国家则在政治上包容、对外开放、充满活力,但它们却相对弱小。因此,海权战略的重点是为了安全和经济利益而控制海洋,并不是为了虚荣而去追求海战的胜利。海权是地中海贸易模式进化的直接结果,每一次海权转移都是海上贸易冲突争执的结果,海权始终掌握在那些拥有先进航运船只和技术的集团手中。
海权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据书中记载,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从叙利亚进口油、雪松、沥青,还有其他造船和建筑用的材料;公元前2000年前后,帆船取代了“独木舟”式的划桨船;公元前13世纪开始,新式舰船的排水量高达500吨。帆船的使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不断扩大的贸易为海权创造了条件,也开创了史前社会较高的海权文明。
海权冲突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早在公元前5世纪,三列桨座战船作为专门用于战斗的舰艇开始在罗马出现。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大流士王组织600艘三列桨座战船把两万军队送到了希腊,这就是著名的马拉松之战。彼时,我国处于春秋时期,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就是战车数量,“千乘之国”乃是大国,而海权国家的兴起也必然以舰船数量相角力。
海权催生了独特的政治制度。腓尼基城市的政治结构反映了商业海洋的目的,它们的国王可能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但他们通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与商业精英分享权力。随着航海距离越来越长,商人们需要资金为投资和进款之间的那段时间提供保障,银行业由此而生,并诞生了金融城市。雅典成为海洋帝国之后,其海权靠的是海洋控制和法庭、巡洋舰和法学家。此时的雅典,已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基本雏形。
海权竞争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存在必然联系。荷兰和英国在全球攫取利益的过程,是其海权利益扩大化的一部分。虽然海权大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海洋国家和大陆霸权之间历史悠久的竞争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海权的贸易属性导致其海军仅为贸易服务,虽然海权最终无力抵抗真正的大陆霸主,但是却引领着现代国家朝向包容,以期实现平等、自由的贸易往来。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本书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海权,强大的海军只是其海洋大陆化战略的辅助,或者说其舰队仍是为国内议程服务的,这也正是海权包容性与美国霸权的区别。
当陆权与海权的冲突日益鲜明,全球格局因之发生剧变之时,“海洋”的地位开始被重新思考和定义,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英]安德鲁·兰伯特/著,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