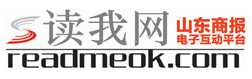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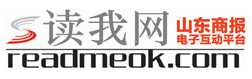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孤独缄默的自闭症患儿又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浪漫称谓背后,语言、认知、社会交往功能严重障碍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随着自闭症患者长大成人、父母逐渐老去,孩子后半生的托管成为每个家庭最担心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帮助自闭症患者融入社会,自主生活,济南五位家长成立了全省首个“社区小型作业所”项目,试点大龄自闭症患者社区托管服务,为“星星的孩子”点亮未来之路。◎文/图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张舒 实习生 韩泓旭

济南“社区小型作业所”托管了4位大龄患者,帮助他们提升自理能力,融入社会
确诊
2007年,30岁的刘元波在紧张和激动中,迎来了儿子大冰的降生。初为人父,他抱着怀中的婴儿舍不得放下。刘元波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因此大冰从小备受家中老人疼爱。
一眨眼,孩子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同龄的孩子很快就会叫“爸爸、妈妈”了,可直到两岁半,大冰仍没有开口说话。渐渐地,亲戚和邻居感受到孩子的异常,建议刘元波带大冰去医院做个检查。“老人们知道后很生气,觉得大冰遭到非议。”疼爱孙儿的老人认为,大冰只是比其他孩子说话晚而已。
直到有一次,刘元波带大冰去医院接种疫苗,打针的大夫听到孩子的哭声后告诉他,“感觉与普通孩子不太一样,建议去做个检查。”
于是,夫妻俩瞒着老人,带孩子去了医院。“当时自闭症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大夫没有察觉到孩子的病因,只是怀疑听力有问题导致不会说话。”结果,听力测试显示,大冰的听觉完全没有问题。于是,医生建议他们回家继续观察,说不定过几个月孩子就会说话了。“身为家长,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康的呢?当时听了医生的建议,挺高兴的回家了,也没有再去其他医院检查。”
又过了半年,已满3岁的大冰依然不会说话。眼看邻居家同龄的孩子都能唱儿歌了,大冰却连基础发音都不会,刘元波坐不住了,夫妻俩决定再次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刘元波,大冰被诊断患有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当时一听,心里顿时松了口气,觉得没压力了。这比我预想的结果好太多。”说到这,刘元波苦笑起来,“现在回想,当时太天真了。”




“社区小型作业所”举办的公益活动让孩子们从家庭中走出来
入学
最初,刘元波对自闭症的认知仅限于网络。当他准备给3岁的大冰找幼儿园时,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一个月内,他和妻子跑遍了几十家幼儿园。就在两人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一家幼教机构答复:“先把孩子送来试试吧。”刘元波说,孩子出生的时候他都没哭过,但接到老师电话的那一刻,他落泪了,“百感交集,直到现在,我都感恩这位老师。”
进入幼儿园的大冰,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很快学会了发声,后来还能表达出简单的词语。儿子的进步,让刘元波看到了希望,“大冰5岁半的时候,我和老师商量,能不能让孩子进入普校(区别于特殊学校的普通小学)学习,老师说不行。”
“都说‘忠言逆耳’,现在来看,老师给的建议非常中肯,但我当时根本没听进去。”刘元波说,老师的话反而激起了他心中不服输的劲头,“我太想证明大冰不比普通孩子差。”在他的坚持下,孩子最终进入家附近的普通小学就读。
考虑到大冰的特殊情况,校方同意刘元波跟着孩子入校陪读。真正体验儿子的学习生活后,刘元波意识到这个决定错了,“孩子根本融入不到校园环境里面,不愿说话,也不愿交流。老师讲课,他坐在下面像是听‘天书’一样,表情茫然。一节课一坐就是40多分钟,还不能动,那种感觉太痛苦了。”入校不到一个月,刘元波就给大冰办理了退学。
“从前心中还抱有幻想,觉得大冰会慢慢好起来。有了这次体验,我才真的从内心深处接受了孩子患病的事实。”于是,刘元波把大冰送去了特殊学校,在这里,有专业的辅导老师教育和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每个孩子会根据病情程度进行对应难度的课程。“大冰在特殊学校里反而适应的很好。他愿意去主动接触其他孩子,也有了朋友。”刘元波说。
担忧
特殊学校实行9年一贯制教育,今年,15岁的大冰马上面临初中毕业。“病情比较轻的孩子,在学校经过学习后,会具备一定的简单技能,可以在部分岗位上就职。可像大冰这样的重度患者,根本不具备自理能力,无法适应社会生活。一旦离开学校,只能回归家庭,由父母照顾。”
大冰被诊断为精神、智力多重障碍重度患者后,为了照顾孩子,2009年起刘元波便辞职回家,“十几年来,儿子就是我的影子,我们从没分开过。家庭开支全靠妻子一人的工资支撑。”
“‘小龄’患儿可以通过特殊学校接受教育,可‘大龄”患儿却很难再找到托管机构。同时,国家针对‘小龄’患儿相对的帮扶政策也比较成熟,针对‘大龄’患儿、尤其是精神类疾病患儿的相关政策还比较少。”刘元波说,随着儿子长大,他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等我老了,大冰的后半生该如何保障?”
抱团
为了寻求情感出口,也为了找到解决方案,刘元波决定和熟识的“病友”家长徐敏星一起建立QQ群,将他们认识的“星爸”“星妈”们集合起来,大家在集体“自救”中共同探索孩子们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刘元波和徐敏星是在一家自闭症康复治疗机构结识的。两个孩子是同一个老师,两家大人们也熟络起来。
“不愿别人拿异样的眼光看帅帅,更不愿他们问起病情。”2002年,徐敏星发现2岁多的大帅不爱与人交流,到医院检查后被告知,孩子患上了重度自闭症。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徐敏星选择让大帅上特殊学校,可初中毕业后,15岁的大帅再也找不到学校接收,“社会上针对自闭症‘大龄’患儿的托管机构太少,价格也高,我们负担不起。”于是,大帅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三年。“大帅将刚叠好的衣服拽出来,刚贴好的壁纸立马揭下来,刚收拾的屋子,他待上几分钟就搞得跟被打劫过一样……”
大帅让徐敏星常常崩溃。直到认识了刘元波夫妻,她像找到了一个情感的“树洞”,第一次有了归属感。于是,2013年,两人建立了“山东省自闭症互助”QQ群,不到一年时间,这个群就从最初的20人迅速增长到1000多人,家长们在群中“抱团取暖”,也共同探索成年“星孩”的生存和教育问题。
成长
2018年,在大帅18岁成人时,徐敏星在群里家长的启发下,萌生了让孩子接触社会的想法。“选择送牛奶,相对简单。一来让他像普通人一样学会一些生活技能;二来让他能够接触外界,更多地融入社会。”担心大帅不适应,徐敏星先独自干了一段时间。
“看起来简单的工作,其实比想象中要辛苦的多。每天4点前必须起床,开始干的时候觉得特别累,第一个月整整瘦了8斤。”她说,第一次上门收订奶费没经验,总是找不到地方,跑重地方也是经常的,“每次送完奶回家躺下就能睡着,连饭都顾不上吃,10分钟就打上呼噜了,后来慢慢习惯了。”等到熟悉工作后,她就开始带上大帅一起送牛奶。
每天凌晨3点半,床头的闹钟一响,她就把沉睡的大帅叫醒。简单洗漱后,母子俩马上出门,赶在凌晨4点前抵达牛奶配送站,领取每天需要派送的300余份牛奶。“天天都送,需要配送哪些都已经记住了。”她负责逐一清点配送数量、核对配送名单,大帅则帮着把前一天的空奶瓶搬回配送站,同时把当天要送的牛奶搬到车上。
徐敏星和大帅所负责的区域,是位于城区北面的老旧小区和略微偏远的村庄。为了节省时间,大帅要把奶送到小区的较高楼层订户的家门口,徐敏星则负责相对较低一些的楼层,碰到电梯房,母子俩就一同上楼。“最开始也需要我陪着一户一户送;熟悉之后,觉得他能认识这个奶箱了,我就站在楼道口等,他自己送,我再确认;最后,我就站在一楼楼梯那,抬头看着他上去。”徐敏星骄傲地说。
“我们大帅可能干了是不是?”“大帅,你真棒!”干活时,徐敏星总不忘给儿子送上鼓励,“你要表扬他,他可高兴了。工作对他就是一种最大的强化。”徐敏星的坚持让大帅慢慢成长,情绪控制能力、理解能力、认知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刚送奶时,大帅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缺乏界限感,上门收奶费时会不经主人同意进到屋里,甚至歪倒在人家沙发上;也有的老人会拿好吃的给他,他不表达感谢拿起来就吃。遇到这种情况,徐敏星就教育大帅:“咱们是给人家提供服务的,到别人家里要懂礼貌。”说得多了,大帅慢慢就懂了。
“自从和社会接触后,孩子情绪也稳定多了。以前他饿了会直接跳起来。坐在三轮车后边的时候,使劲儿用头撞我的后背,导致有一阵儿,他一有情绪,我就条件反射似的后背疼。”徐敏星说,“现在,我敢带他出去了,在见朋友、聚会吃饭等场合,对一些更高级的情感,大帅也能体会并作出反应了。”大帅开始对人感兴趣,大人聊天时,他会静静地听,聊得开心时,大人笑,他也会附和着笑一笑。
集体
徐敏星说,在儿子的成长之路上,她走了太多弯路,“干预、引导得不够科学,导致儿子很多年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在干预上,家长明显操之过急、拔苗助长,有时难免打骂孩子,给大帅的成长造成了二次伤害。”
于是,为了让更多的患儿家庭从“自我封闭”走向集体,也为了解决大龄患儿的社会保障,徐敏星决定和以宋湘敏为首的家长们携手“向前再走一步”。
2016年,宋湘敏、徐敏星等自闭症患者家长共同创办了“星星缘”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组织,并在济南市民政局进行了登记备案。他们开设了微信群,从民政局备案的自闭症家庭中一一打电话联络,与5000多名患儿家长建立了联系。
在大家的相互接触交流中,宋湘敏发现,“很多家庭崩溃的最主要原因是大人不接纳,希望把他改成一个正常人,这反而对孩子是一种伤害。”她说,“还有部分家长病急乱投医,给孩子服用各种精神类药物,花费四五十万元的不在少数。”
希望
宋湘敏说,她发现很多家庭会选择把患儿“藏起来”,自我封闭式保护孩子,断绝孩子和外界接触的渠道。“所以公益组织最初的定位是让孩子们从家中走出来,让社会逐渐认识和接纳孩子。”最初的几年,多种新颖的交流形式很受家长们欢迎,“我们举办过各种公益活动,组织‘妈妈合唱团’,带孩子们去植树、捡垃圾,请教育专家来举办公益讲座……”
但是两三年后,公益组织很快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相互之间没有倾诉的欲望了,组织成员开始大量流失。”宋湘敏说,参加互助活动的家庭从最初的一百多个迅速减少至十几个,“最少的时候,来参加活动的只有几个家庭。”
成员的递减,让宋湘敏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帮助大龄自闭症家庭的方法。于是,宋湘敏将眼光放到了外省。因为女儿贝贝也是自闭症患者,18年来,为了给贝贝治病,她跑遍了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医院和相关机构,也因此结识了不少“病友”家长,并由他们引荐认识了外地的相关公益组织。于是,宋湘敏自费出差,到处学习公益组织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这时,“社区小型作业所”项目进入了她的视野。
所谓“社区小型作业所”,是将特殊患儿托管机构建设在小区或社区之内,通过对患者实施“精神慰藉服务、能力康复训练、支持系统建立、辅助性就业援助”等系列举措,帮助他们提升生活自理能力与社会融合能力,让他们与社区居民和平共处。“社区小型作业所”针对的托管对象,正是宋湘敏女儿这类已经成年的大龄自闭症患者。
宋湘敏带回的“社区小型作业所”项目信息,也让刘元波、徐敏星看到了孩子未来生活保障的希望。2016年10月,宋湘敏、刘元波、徐敏星、赵昆、徐景波五位大龄自闭症患者家长,成立了全省首个“社区小型作业所”项目,在阳光新城社区试点大龄自闭症患者社区托管服务。五人中,宋湘敏、刘元波专职负责照顾孩子们。目前,“小作所”共托管了4位大龄患者,年龄从14周岁到24周岁不等,主要针对精神残疾、智力残疾的人群。
对于宋湘敏而言,托管绝不仅仅是照料饮食起居,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社交能力,“要以人为本,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和正常人一样活得有尊严。”宋湘敏的女儿贝贝刚来的时候,“一直走来走去,从不坐着,与人交流为零。”现在,她已经在“小作所”里交到了朋友,建立了友谊。
“建立探索‘小作所’模式,也是希望能以此试点,争取政府政策支持。”宋湘敏告诉记者,现在“小作所”的开支主要依托托管费用、基金会支持和部分创投资金,老师们都是患儿家长。她希望,未来,这个试点能得到“爱心专家团队”或更专业的康复师的帮助,来不定期指导和培训老师;也希望政府的介入能为“小作所”指明未来发展方向。
“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走出这里,走上新的人生轨道,寻找到更光明的未来。”与记者分别时,宋湘敏紧紧牵着孩子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