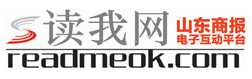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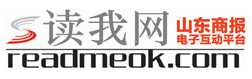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郑从彦
没有一位书写者二十四小时都是书写者,但著名杂文家、作家、评论家徐迅雷先生不仅全天候关注新闻时事,而且瞻“前”顾“后”——既回望历史,又展望未来。他以极其罕见的旺盛精力,创作一篇又一篇重要的启思之作,最终汇编成新著《太阳底下是土地》。这是继《这个世界的魂》《温柔和激荡》之后,作者出版的第三部人物随笔集。
书写人物,有时就等同于记录一段个人历史,当然也顺带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侧影。歌德曾经虔诚地称历史为“上帝的神秘作坊”,此言非虚。徐迅雷先生就在这个作坊里挖掘出诸多陈年旧事,虽然99%都可能平淡无奇甚至毫无意义,但是难忘而崇高的那1%,恰好成为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高光资源。这里有历史人物的再现,这里有现实(最新的历史)人物的闪耀,这里甚至有未来(即将成为历史的历史)事件的畅想……天空没有止境,太阳底下是土地,土地之上是一和万物。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土地,便是孕育神奇生命的地方。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往往几百年方能出现一个天才;而对于一本书而言,它可以汇聚所有人类星辰的闪耀。伍连德,中国百年战“疫”第一人,他为中华民族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历史性的、开拓性的、里程碑式的,是一个站在土地之上的大写的人。梅藤更,从鞠躬到尽瘁,广行济世,广慈博爱,济人寿世,救死扶伤;以45年之韶华,将优渥的情怀洒满中国杭州的每一寸土地。贝聿铭,借“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慨叹一生行将告终;殊不知,不朽的贝氏建筑,是艺术觉悟、文化觉悟和文明觉悟的结晶,是艺术和历史在大地之上的完美融合。在徐迅雷的文字沃土上,那时那人那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真正意义深远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时间的酝酿,真正出类拔萃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土地之上是太阳,众人都看到太阳射出的万丈光芒,但徐迅雷深知烈日灼心,伟大的背后皆是磨难。樊锦诗刚来敦煌时,迫切想看洞,可是“洞外面很破烂,里面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这么爬下来,很可怕”。廖智坦言:“我如果不经历灾难,就不会对受灾的群体有这么深的同感;我如果没有截肢,就不会对残疾的群体有这么强的使命感,这是苦难、患难对人生的意义。”从天空到大地,是读者阅读俯视的自由;从大地到太阳,恰反映徐迅雷写作仰望的艰辛。多少人物,需要陟罚臧否;多少往事,需要重新审视;多少思想,需要再度解放。
徐迅雷驾驭语言十分纯熟,众所周知他以评论见长,因此在常规记述之外,总不忘点评一番,这样的习惯立马使其笔下的人物变得愈加形象、生动、具体。最后就是徐迅雷总是把自己的经历巧妙地融入人物随笔中,如此一来,一是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二是他以这样的方式观照自己的灵魂。毕竟,和那些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相比,徐迅雷先生始终是一个用博爱和人文关怀来观察整个世界的人。
太阳底下是土地,一字以蔽之,曰:旦。破晓时分,旭日东升,土地之上是希望!
(《太阳底下是土地》,徐迅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