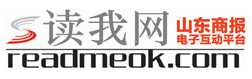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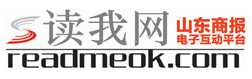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近日,作家愚石长篇小说合集“乡望三题”由山东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乡望三题”收录了愚石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3部长篇小说《乡志》《人子,人》和《天虫》。3部作品均先后被列为中国作协、山东省作协年度重点扶持和定点深入生活作品,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山东省改革开放40周年40部优秀鲁版图书、“中国梦”长篇小说一等奖等殊荣。合集出版,日前,记者专访作家愚石。◎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文学是梦想、是发现真相的重要方式
记者:您与文学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愚石:当作家对许多人来讲都是一个瑰丽、诗意的梦,尤其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最初想当作家,是因为老师经常拿我的作文当范本,在课堂上朗读。那时,如果有哪一周的作文没有写好,我就会很难过。高一时,《少年作家报》刊登了我的小短文,真正点燃了我当作家的梦想。我开始读一些文学经典,写一些自认为优秀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彼时,正是“强说愁”的年纪,写的东西充满了青少年时期的漂泊感、无助感。现在回头去看,那时的东西根本算不上文学作品。
记者:那么,文学创作对您来说是什么?
愚石:在不同阶段,我对文学的认识是不同的。高中和大学阶段,觉得文学可以成就自己的梦想,所以追求得狂热,并无确实的方向。工作之后及至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创作成为我观察生活、体验人生、发现真相、开掘灵魂的重要方式,写出的东西也是现实主义的,言所思,抒所虑。到了现在,文学是我活着的方式之一,无论鲜活或者消瘦的生活,我都想从生活的原初和朴素出发,在文学作品中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独立、灵魂的迥异、思考的多维、人性的温暖。
记者:您不是专职作家,如何做到创作与工作和谐共处?尤其是从事长篇小说创作,您又是如何利用“时间”来进行素材的收集、整理的呢?
愚石:常常有人说,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其实我更想说,发现美的眼睛到处都是,比如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了抖音快手的创作高手。但生活中真正缺少的,是记录生活的一只笔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
可以这样说,我的生活全程,即是我积累创作素材的过程。我的工作笔记就是采访笔记和素材绘本,为我的小说创作积累了随时随地的美丽和感悟。比如《乡志》,我用3年的工作日志,再加上一整年每天几千字的创作,才有了现在的模样。有人评价这是一部乡村寓言,一卷历史长诗,是我几年基层工作的文学性再现,也是喟叹于时代与乡村的心血雕琢。必须承认,这部小说正是以2007年为纪年,记录下鲁中南乡村的原初生态,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一一呈现和展示,以时代交替揭示“变”的痉挛与阵痛,最终构建起以人性、道德、价值观为基准,追求民主、民生、民意公平自觉的文学经纬。至于创作时间,我的经历告诉我,只要能够挤出一些喝酒或交际的时间,把创作计划化整为零,再将作品化零为整,就可以了。
望故土能够成为文学志士的向往之地
记者:您出版多部长篇小说,如“乡望三题”,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您认为写作长篇小说的重点是什么?
愚石:文学创作的核心是人,创作者、刻画的对象和读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打通“人”与社会情势的勾连细节,处理好“人” 与复杂社会的矛盾关系,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结构和语言体系,对作家而言是最困难的。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既要写出人与社会的纵深与平阔,又要创造出具有作家独特语境、独立思考下的形象概括,既要写出多层罗列的社会群体的复杂性,又要写出微不足道的生命个体在复杂性笼罩下的典型性和唯一性,这是小说创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比如我在创作小说《人子,人》时, 以木偶传承人的一生为主线,叙写了主人公“戏里戏外,他总在戏里”的生命境况。其中,毁灭与生存的角力,构成小说人物的生命元素和悲壮底色,也让读者在作品中完成了一次厚重而浓烈的精神苦旅。
记者:起名“乡望”,有什么寓意吗?
愚石:《乡志》《人子,人》和《天虫》是我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在创作之初,我便构思规划了自己的长篇三部曲,即乡志、县事、家言,并据此将工作、生活和创作实践有机结合,力争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写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文化传承的现实主义作品。随着时光流转和创作意图的渐进优化,我个人的创作思路更加清晰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乡望三题” 的创作蓝图。从《乡志》开始创作的2008年算起,至文集最后出版,已悄悄浴沥过12年光阴的沉淀与砥磨。正所谓“桑梓写疏篱,回首已半生。”
“乡望”一词,有几层含义:一是对故乡的回望,我要用这几部作品,记录我的乡音乡愁;二是对家乡的美好期待和深情期望,希望自己家乡的人情风土,都能够如诗如画,希望我的乡亲父老,都能诗一样栖息和生活;三是我想以此表达自己的文学梦想,希望故土能够成为文学志士的向往之地。
记者:您的作品与鲁中南的风俗人情、乡土地域有关,您认为它们在您的创作中的作用是什么?
愚石:从我出生于这片丰饶美丽、充满艰辛的土地,我便与故土须臾不可分离。
家乡的风俗人情,成为滋养我的庄稼,也成为强壮骨骼的营养,让我的小说更多了人情冷暖、道德关怀和终极梦想。比如《天虫》,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蟋蟀为主题形象和生命背景的宏大长篇。这部书,有人评论像一部阐述区域历史与文化景观的宏阔史诗。我只想通过这部书,传达一种创作的意旨:虫活百日,人活一世;虫即是人,人亦如虫。自然大道与命运悲欢,只不过是瞬间,不管辉煌还是失意,都在方寸栅罐之间,向死而生,泣诉如歌。我力图实现的创作意念,正是在一点点展开的人情画卷中,慢慢实现的。
文学创作没有终极目标
记者:您认为乡土地域、风俗人情等,它们与创作的关系的把握和处理,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愚石:对作家而言,所有的风土人情都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可以化为作品的血液,也可以成为作家头冠上的彩珠。对这些地域风情,不能简单地记录,要将其化为无形,成为文学的细胞,丰富创作的枝干,要成为自己独特的表述平仄,活跃语言的节奏和韵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域风土交给了作家无数的宝藏,作家要发掘好、保护好、传承好,更要使其得到升华和淬炼,以文学的诗意反哺地域、反育故土。
记者: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能分享下吗?
愚石:我正在精心修改一部新的长篇《往生》。这是一部给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的作品,也是献给父亲的作品,献给我的父亲,大家的父亲。可能好多人没有注意到,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篇写给父亲的祭文。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岁月中,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作为大队书记的父亲,作为革命战士的父亲,一直活得像三条不同流向的河流,偶尔在某一个汊口相遇、激荡、碰撞,又迅速消解。”小说强调“我盼望着的所有和解,大姐之于父亲,父辈之于历史,曾经苦痛沉重的生命个体之于国家和时代……是生与死的交替,是父与子的交接,是生命个体与宏阔世界的终极和解……给我的儿子和后生们,留下灵魂力量和血脉传承。”我相信这部书,一定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奇和欣喜。
记者:您的作品不仅备受读者喜爱,更频获文学大奖,您的创作路有终极目标吗?您认为,未来如何走?
愚石: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没有终极目标,只能是一直在路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景,不同年龄亦有别样的胸怀。不管怎样,我都会以作家的良知和创作可能,以强烈的历史叩问和责任担当,迎风站立,不惧尘埃。我也必定坚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人文,创作出仅属于这片热土和家国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