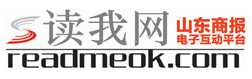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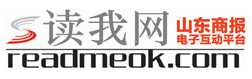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山东70后女作家于琇荣最新长篇小说《南风歌》出版,小说以古老村落枣林湾为背景,用70多年的时间跨度,讲述了老农民谷子青祖孙三代致力乡村振兴,带领村民奔小康的故事。书中详细叙写了中国粮食、土地峥嵘史诗般的发展历程,并通过个性鲜明的人物命运,对农村、农业、农民、农田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描绘了一幅鲁西北平原农耕文化的人情风物变迁史。近日,记者专访于琇荣。◎山东商报·速豹新闻记者 朱德蒙

因“孤独”走上的文学创作路
记者:您写作了多部作品,是什么影响您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呢?
于琇荣: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诗歌《叶签》时是17岁,当时并没太惊喜,仿佛那是件等待了很久自然而然本该发生的事。
每个写作者都有踏上写作之路的理由,我也不例外。致使我走上这条路的无外两个字:孤独。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我拥有了丰盈、独特的人生体验,尤其是父母工作调动期间,我被迫休学在农村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生活巨大落差以及因水土不服造成的困扰让我变得沉默、敏感。我穿起一层一层坚硬的铠甲躲避人群,掩饰内心的胆怯恐慌,每天在对死亡的恐惧中迟迟不肯睡去,又在每个黎明到来之际为重生欢喜。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陷入这样的境地,是事情本该如此?还是人为使然?那时的思索和追问延续到现在的写作风格,使自己在传统陈述事实存在本身的同时,增强了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以及自我觉醒的成分。后来,我笃定地选择了写作——世事芜杂,语言太假,如果一定要表达,我宁愿选择一种相对客观永恒的方式。
记者:这条写作路,“景况”如何?
于琇荣:剔除一些微不足道的文学成绩和奖项,写作带给我的欣喜时刻,莫过于一篇作品完成的瞬间,那种充实、满足和快乐。虽然很短暂,但足以抵消创作的漫长、枯燥以及孤独思考的痛苦。
对我而言,创作过程遇到的挫折瓶颈,一个是焦虑,对时间的焦虑。时间太快了,为此常常熬到午夜,不肯轻易放过“今天”。这种情况在粮食局工作时尤为明显,白天带着科室人员下乡粮食执法,晚上利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时间写点散文,而小说一般只能等到周五、周六熬通宵来完成。随着年龄增长,我告诫自己“人生短暂,不可心存贪婪面面俱到,必须要做出选择。”幸好,我选择了写作。
很多作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连续输出耗尽了之前的知识储备,各种灵感都会感觉枯竭,经常是处于写不下去的状态。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选择独处看书,或做些别的事情,过段时间有感觉了,再继续写下去。但当写的特别顺的时候我也会警醒,不要落入自己惯性写作思维和模式。
记者:您在这条写作路上的目标是什么?
于琇荣:创新、颠覆是我写作一直追求的方向,浅表性、故事性文本因为好读易懂而传播广泛,但我觉得这不是严肃文学唯一或最好的表达方式,文学绝不仅是简单的描写、叙述或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还有观照、延伸以及隐匿在事物后面的隐喻,文学探索的不是真相,而是事情本身的前置和后延,这样的作品不仅是用来“读”,更是要“悟”。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乐趣所在。
以刚完成的短篇小说《折耳猫》为例:作家马洛因作品格调残酷悲观被认为是冷漠的人,为了改变,他在写这篇小说之前就告诫自己,一定不能把人写死。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最后留给主人公小安的结局就是:心存恨,能活;存爱,不能活。
文本以现实和虚构小说两条主线交叉推进,只为阐述一个道理:善良、爱不是说出来的,只有看到人性的丑陋、阴冷,才会去爱,才懂什么是爱。
迄今最为满意的一部长篇小说
记者:长篇新作《南风歌》出版,您能谈谈新作吗?
于琇荣:《南风歌》共计35万字,书名取自先秦的一首歌谣。这部小说承载着我多年的心愿,对我有着别样的意义,是我耗时最长、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小说。当然,在一部作品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标志着作者的任务已经完成,至于好与不好,要交由读者评判。但毫无疑问,它是我迄今最为满意的一部长篇小说。
写这部小说的念头起自粮食局工作期间,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始终关注中国粮食和土地问题,其中,我更关注转基因粮食,它的品种、播种面积、种子研发、供应渠道等。无论科技怎样发展,我还是倾向于作物自然留种,而非人为干预的杂交种子,当然还有土地板结、耕地过度消耗,以及互害式种植等,总之,我对土地、粮食的所有思考都隐匿在文字里,借一个老农民的命运加以阐述。
这是一部全面反映近50年来中国农村政策变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古老村落枣林湾为背景,用70多年的时间跨度、空间维度,讲述了祖孙三代致力乡村振兴,带领全体村民奔小康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展现了农民在土改、互助组、生产队,到改革后的分田到户、土地流转、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历史节点中发生的重大变革,并通过人物命运,对农村、农业、农民、农田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阐明了粮食和土地是中华文明根基所在的道理,在反思农业与工业两种文明互补与冲突的基础上,描画了新的农村土地政策在当今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小说以较大的体量,阐释了人与时代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有对人民体恤和煦育之情,也有人民对时代赞颂和祈盼之意。正如先秦歌谣《南风歌》所写: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乡土文学需要调整观念,顺应时代
记者:很多人讲新语境下的乡土文学创作,您如何看?
于琇荣:“乡土文学”的创作,在整个2O世纪可以说成绩斐然,影响深远,也造就了一大批知名的作家,但在崭新的语境下,乡土文学正逐渐失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片段式”阅读,城市化进程推进等大环境的影响,让乡土文学失去了可以产生共情力的读者群;另外就是乡村早已不是古朴、沉寂带着淡淡哀愁的贫瘠之地,固有乡土意识与正在变化中的乡村产生了隔阂。但这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没了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关键是如何调整观念,顺应时代。
在《南风歌》中,当时间轴推进到2018年时写到:解冻是春天的先兆,空气中有了土腥和阳光的味道。一缕熟悉的香气从窗外飘来,它有时悄悄的在身边变得十分浓郁,有时又似乎被风带到触摸不到的地方,虽然大片金黄的花田还没有在眼前盛开,这股如影随形的香气似乎已踏上奔向四面八方行驶的列车,所到之处都听到那种带着欢笑的消息,不胫而走地散布在各个村庄——乡村振兴来了。村容村貌仿佛一夜之间换了新装,粉白的墙,整洁的巷子,丰收的麦浪和笑容可掬的送福娃娃一起被绘制在街道墙体上,每个从路上走过的人都有种身在画中游的恍惚感——幸福来得太突然啦!
乡村已不是“老树枯藤昏鸦”,也没了“迟迟朝日上,炊烟出林梢”图景,人居环境整治让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无法回避的时代痕迹。但根植在内心的乡情、对土地和庄稼的热爱是不变的,对爱的理解和渴望是不变的。
其实乡土题材对我是有些难度的,首先没有乡村生活经历和经验,单凭僵化的资料是行不通的,我便无事就开车在乡村、田间转,遇到人就天南海北地聊,我相信,无论“乡土文学”还是“先锋文学”,无论传统还是意识流,归根结底是写人,是挖掘人性本真特质。我感觉恰是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置身平视的立场,不拘泥,有了更广阔的素材搜集空间。所以我想,以深邃的思想空间,用全新的文学品质来应对挑战,乡土文学应该还是有广阔市场的。
记者: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于琇荣:现在正在写一部散文体长篇小说《大风吹过山海关》,已完成三万多字。如果《南风歌》是一部乡村史,那这部则是城镇发展史,重点挖掘人性在欲望诱惑下的复杂性,无论善恶、美丑,都将真实呈现,也算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在此之余,继续短篇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