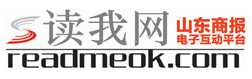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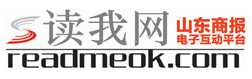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 热门搜索关键字: | 读我网 鲁商集团 | 鲁网 |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8年,莫言推出最新小说集《晚熟的人》。日前,莫言携新书首次走进直播间,与读者们分享新作。他说,与这么多人互动非常感动,以这样的方式与读者交流还是第一次。随后,他和诸位嘉宾就新作、“流量时代”的文学价值等话题进行探讨。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记者朱德蒙实习生莫非

谈新作丰富感受以文学方式表现
莫言新作《晚熟的人》,被业界评为“如同获奖后记”,莫言将自己写进小说,用幽默的笔调,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诺奖后的生活里外。全书共12个故事,故事中有喜有悲,有荒诞亦有现实。读者可以随着故事中的“莫言”,见证一次“衣锦还乡”之旅,也见证百态人情,万象世间。
谈起写作新作缘由,莫言表示,作家要写什么,有时候并不完全由作家自己作主,“我简单回顾一下我的创作历史,我曾有很多幻想,一会儿想写天文,一会儿想写科技,有时候也想写童话等。但有些要写的东西不允许我去写我幻想中的东西。所以写《晚熟的人》里面这样一系列的故事,因为这些人物,有的就是我的朋友,有的甚至跟我像孪生兄弟一样的彼此的知己。这七八年来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仿佛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才能把我自己的这些丰富感受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
至于起名“晚熟的人”,莫言则解释,晚熟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学或者艺术角度来讲,一位作家或艺术家过早的成熟、定型,那么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变化,希望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但超越自我难度很大,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大家都不希望自己过早的定型,即不希望自己过早的成熟。可以晚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创造力能够长久一些。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籍作家首位获得者。2020年,距获诺奖已过去整整8年,距莫言出版上一部小说也已过去10年。有人说莫言陷入“诺奖魔咒”,获奖后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
随着《晚熟的人》的出版,再谈“诺奖魔咒”,莫言表示,“魔咒”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获诺奖的作家一般都年龄很大,他们的创作巅峰期已过,有的人甚至获奖以后没几年就告别了人世。但也有很多作家在获奖之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如马尔克斯,他获奖后写作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等是至今仍被我们阅读的了不起的著作。所以,我能否超越自己,能否打破这个魔咒,现在不好判断,但我一直在努力。8年来尽管我发表的作品不多,但我还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做准备,也就是说我花费在案头上的准备工作,远比我写这本新书的时间要多。”
相比万众期待的长篇小说,此次,莫言新作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因此有网友质疑“中短篇写起来是否更容易”。莫言表示,这是他一直感到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大部分读者包括很多评论者,也都认为一位作家,只有拿出一部长篇来,仿佛才能够证明他的才华,证明他的力量,“但我们也都知道鲁迅没写过长篇,沈从文也没写过长篇,国外的作家没写过长篇的伟大作家更多,像莫泊桑、契诃夫等。一位作家一辈子不写长篇,只写中短篇,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文学的贡献。当然,我们应该承认,长篇小说无论从它的体量、广度和深度、反映生活的丰富性上,确实超过了中短篇。我没有把中短篇和长篇对立起来的意思,我觉得这三种形式是不可替代的。我也有一个长篇梦。我确实也希望能够在最近几年里拿出一部好的长篇来。假如要写一部长篇也不是特别困难,半年时间一定能写完,但我想,如果要写,是不是写的和以前不一样,是不是和以前的艺术水平相比较更高?这个很难说。我在努力。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拿出一部让大家看了以后有一点点耳目一新的感觉的长篇小说吧。”
谈信息化用最普通的语言把故事讲好
10年未有新作问世,当年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年轻,小读者也已成年。当被有的读者问及“是否需要很高的文学素养才能看懂您的书”时,莫言笑称,如果是自己年轻30岁时写的小说,可能会读不懂,但“我现在写的小说,你肯定可以看懂。
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追求各种各样的西方流行的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但随着人的慢慢成熟,才意识到用最普通的、最平常的语言把故事讲好,才能够显示出一个作家真正的成熟来。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老少咸宜。”
随后,谈起近年关注的一些作品时,莫言表示,近两年,自己一直在阅读地方志,“譬如我老家周边的十几个县市编写的文史资料,因为这是很多人对他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回忆,让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最近两个月,我去了老家高密,以及诸城、胶州、平度、青州、安丘等地,去年则去了蓬莱、龙口、乳山、海阳等地。我每到一个地方先搜集这个地方的地方志,然后再看这个地方的博物馆,看一些所谓的名胜古迹。这样一种既有对文字的阅读,也有对自然景观的阅读的方式,会让你真正深入到一个地方的历史的深邃之处。假如要写历史小说的话,我想这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
莫言透露,他也有微信,有朋友圈,也会看,但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我过去认为,只有城里的年轻人在玩手机,在利用手机,利用网络。但现在我发现根本不是,农村的人在网络时代也突然成长起来。过去农村信息比较闭塞,交通也比较落后,也许一个人一辈子没到过县城,没坐过火车,这种人在我的父辈里面比比皆是,或者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如果按照过去的年龄来衡量的话,都是很老很老的人了,但恰巧是这些在过去被认为很老很老的人,现在他们对网络的熟悉,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跟城里的年轻人同步的。
所以,在我小说《红唇绿嘴》中的那个人物,她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她也有非常曲折的、不幸的人生经历,吃过很多苦,干过很多不太好的事情,被人欺负过,但是这样一个人在当下没有变成一个科技盲,而且比很多年轻人更知道网络能给她带来什么。这样一个人物在过去我的小说里从来没有出现,也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正是时代造就的一个人物。”
莫言说道,如果读者能够从书里面读到自己的身边人,或者读到自己,这对一位作家来说是最大的安慰,“我们作为读者之所以能够被某些书打动,甚至为书中的人物命运而担忧、痛苦,那就说明这本书里写到了我,它具有典型的高度概括力,确实是作家塑造这个人物代表了很多人,写出了很多人共同的感受。”
自称是一位没有什么生活趣味的人,若不写作就读书,不读书就散步。但莫言还是表示,近些年,当自己看到中国很多作家也纷纷拿起笔来写字、画画时,特别欣慰,“我甚至曾狂言过,不用毛笔写字是理解不了古人的,是看不懂《红楼梦》的,是读不懂唐诗宋词的,只有你拿起毛笔书写的时候才能跟古人站在同样的高度思想。当然这是文学的语言,略带夸张。但是这么多位作家、艺术家,都拿起毛笔、拿起画笔,在自己的写作之余进行一种书写,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学习和训练,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寻根,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尤其是今年,受疫情影响,很多孩子只能在家里上网课,莫言表示,如果家长没有音乐方面的才能,也没有美术方面的才能,能教孩子什么呢,“所以,我们来背唐诗、背宋词吧。我想,今年唐诗宋词对孩子们的教育,应该是比过去两年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