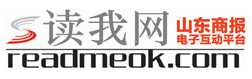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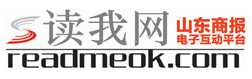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2020年5月,继2009年出版《我与父辈》之后,暌违10年之久,阎连科新作《她们》终于与读者见面。《她们》是阎连科书写家乡女性的长篇散文。新书上市,作家亲写长序“十年的等待”,并通过出版社向读者动情推荐。山东商报·速豹新闻记者朱德蒙
有些写作是年年不忘的等待
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客座教授。其作品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阅读和传播。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也是继村上春树后,第二个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亚洲人,被誉为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
一。
继2009出版《我与父辈》10年之后,阎连科于今年推出全新长篇散文《她们》。书中,作家通过描述自己家族的女性命运,窥见几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境遇。这里,不仅有母亲、姑姑们等母辈的人生故事,也同辈姐姐、嫂子们的生活,以及与孙女辈的点滴相处。提起《她们》的创作,阎连科在新书序言中坦言:“写一本薄薄的散文,需要10年的等待,这是一种微笑的隐痛。”原来,在写完《我与父辈》后,出版界的朋友曾希望他就高趁热,再写一本关于家族女性的书。但大作家并不想把家族中的女性写成父辈一样的人,因为“她们在那一片屋檐下,在那些院落土地上,在时代的缝隙尘埃间,说笑、哭泣、婚嫁、生子并终老,然后她们的女儿又沿着她们走过的路,或者找寻着自己的却也是众多‘她人’的路,期冀、欲望和奔波,发达或坠落,沉沦或疯狂,呼唤或沉默。……我无法明白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之所以是着人,也才是了如此这般的女人。命运于她们,既是一块放开的阔地,又是一羁逃不开的囚池。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她们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关于父辈和我和别的男人们,我似乎是清晰知道的。关于母辈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们,还有这之外的‘她们’,我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
所以,无从知也就无从写,厘不清也就等待着。这一等,就等了10年。
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创作
直到有一天,阎连科突然明白了,那些他所熟悉的“她们”,与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度里所有的“她们”并无本质不同,她们都是一样裹挟在这个时代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和营生。于是,10年念念不忘的等待和煎熬,终于落笔成文。
阎连科说,千万不要把《她们》理解为他的一部自传小说,甚至也不要理解为他的“非虚构”写作,“我认为非虚构写作,应该更偏重与人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但散文,则更偏重个人情感化和内心化。简言之,散文更多的是面对个人的世界,非虚构更多的是面对他人的世界。《她们》我是当作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去写的。同样,什么样的家庭,是原生、非原生抑或其他什么样式,对作家的成长和写作都会构成一种影响。莫泊桑从小父母感情不和而分居,他一直跟着母亲成长并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莫泊桑。普鲁斯特家境很好,但他是一个极度敏感脆弱的人,幸运的是,他的母亲给了他无边而细腻的爱。弗兰纳里·奥康纳16岁时父亲死于红斑狼疮,使她的人生极度痛苦和艰辛,因此她成为了特别能面对丑恶、黑暗的写作者。……家庭不是作家成长的土壤,但什么样的家庭对于作家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书中,作家写《母亲》一篇:小时候,觉得母亲语言罕寡,句句真理;中年后,觉得她说话更少,重在木讷了。到现在,又觉得母亲口才甚好,自立逻辑,并且表达任何物事和理道,都有自成一派的言说风格和思维方式存在着。原来所谓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与过程。……字里行间,是一位儿子与母亲的牵绊和依赖。“车轮滚滚,人生如流。从书中,我们可以看见生命的延续与岁月的变迁。”关于《她们》,该书责编指出。
有意思的是,除了写母亲、妻子等“她们”,阎连科也提到了他的“相亲对象”,而相比与妻子话婚姻和生活的略微的小唠叨,写相亲对象时,作家就轻松活泼了许多。他说:恋爱如盛开在那个季节中的泡桐花,美得宛若一场尴尬而壮观的笑。
对此,阎连科表示,作家的自省,正是一种坦诚和真实,“我们无论做文还是做人,一定都希望和实在人待在一起。和实在人一起心里踏实。表现在写作中的实在,就是坦诚、真实、不虚伪、不做作。一句话,写作敢于面对某种真实,就是一种自省。所有敢于面对真实的作品,一定是敢于自省的作品。我不能说我的作品多么自省,但我确实在写作过程中,是真实的、实在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尤其是在散文和非虚构这样的写作。”
借此思考地域和时代的文化差别
文学史上,一直不乏对于女性的书写,作家们通过描写女性的形象、书写女性的命运,来反映特定时代下女性的生存境况和思想转变,并以此洞悉一系列社会问题,反映一个时代生活的真相。“
《她们》是写了几代的女性,但一定要记住,它是写了那块土地上的几代女性,是那种文化上的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很简单的思考。那块土地上的女性,当然,也是中国女性的参照和缩影,但中国太大了,南北文化的差别、城乡文化的差别,沿海地区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别,内陆地区和边境地区文化的差别,还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别。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决定着女性的差别。我所幸运的是,我是河南人,河南是中原地区,这儿的文化在中国有一定代表性,所有这块土地上的女性,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阎连科表示,尽管自己不能为中国女性实际做什么,但如果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让大家多几分理解和尊重,“那么,我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
时至今日,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一直是被讨论和关注的热点。对此,阎连科澄清,一定不要说他对现代性别理论有贡献,“在第六章的开篇我就说,一定不要把这一章当作论文看,一定要当作散文、随笔读。当然,如果‘第三性——女性之她性’,能引起对现代性别关注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的关注,我会感到欣慰,非常开心。同时,如果散文、随笔有了某种‘理论’功效,那么散文和随笔,作为文学体裁也算拓宽了固有散文的僵界。在散文僵界的拓宽上讨论《她们》,我会比较踏实。如果说拓宽了现代性别的理论,我会很不安、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