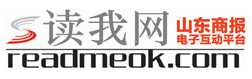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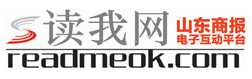



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的信息时代,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处于式微状态,取而代之的是观念、行为、装置等艺术现象大盛。数量越来越多、风格形式越来越繁富的画作背后,我们却难以寻觅打动心灵的倾情之作。现实主义艺术在当今还有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国画如何与当下文化语境结合呈现独特的审美意义与价值?李兆虬先生的“新现实主义”表现性水墨国画作品给出了个人的思索与探究。
李兆虬苦苦探索的“新现实”表现性水墨国画,应该看作当代现实主义艺术在国画领域新的表现形式,它在内容上关注社会现实,在形式语言上运用具像写实与抽象表现的手法,直接和广泛地描绘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物形象塑造从英雄化走向平民化;写实手法也发生嬗变:结构性笔墨刻意回避了素描性笔墨的程式,相对自由随意而内含生命力的笔墨组合刻划捕捉对象生动的感性特征,并达到笔墨自由性与形象真实性的统一。兆虬先生在艺术实践中注重增强画面的结构的整形与力度,以拙、涩和粗糙感处理用笔和泼积皴染的块面,笔墨自身的独特意趣刻画营造出特定的气氛,保留写实性的写意方式,通过墨色的对比、过渡与交融,精妙地构筑笔墨、造型与意境的和谐统一,从民族传统和外来艺术中广为借鉴经验和技巧,虽高雅而不冷峻孤傲,洋溢着一种儒雅之气、学术之风。
兆虬先生的出生地高密县,盛产享誉海内外的扑灰年画,其以色代墨的艺术特色独树一帜,将其拿来并反其道而为之,尝试以墨代色的技法,以图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艺术的沟通与对接——绘画语言在兆虬先生的思考、探索下,从传统的绵延、断裂、变异,他最终选择扬弃那种陈旧的笔墨与造型关系,更多地承接着新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水墨思绪,即拆解笔墨的时序性,强化笔墨的空间性,打造画面的视觉动感,营造画面的视觉图式。他以追求和审美性、规范性相反的粗笔险墨来呈现他的心里图景,与现实物象拉开距离,建立自己的水墨心象。表明他对历史抉择的姿态,恰如其分地表达当下都市文化心理。兆虬先生的《王贵与李香香》正是探索过程中的标志性成果。王贵与李香香人物形象在绘画语言上,强化画面的平面结构与气韵的流贯,追慕整体浑然与大气的美感,实现了由写实到写意的转变。兆虬先生开始以性灵驾驭笔墨,强调运笔与施墨新鲜活泼的性情化与灵感性的创作旅程。他此时的艺术选择,决不是出于廉价的猎奇与怀旧情绪,而是对自身水墨艺术的重新把握,一种审美因素的唤醒,一种追求生命无限感和永恒感的表现——过去表象的典雅与流畅从他的笔端消失了,“语言”诗意转化为内在的韵味,作品结构紧缩而有力,有时呈现出貌似无序、粗鄙的状态,气韵生动中显露出的苍凉与犷悍的画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题旨——生命的艰难与悲壮,这种浑然与大气的美感,体认生命的顽强与坚韧,让人领悟到一种深沉与力量。
近两年来,兆虬先生将注意力转向了寻常的都市题材,在他笔下所反映的大都是他身边的男女老少们的喜怒哀乐, 其作品更加注重绘画的形式感,刻意追求有意味的造型形式,通过司空见惯的客观物象来表达一种超乎象外的主观情结,此主观情结的视觉形象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为具象,又为抽象,有意识的把自己的艺术置于精神层面上的思考。兆虬先生虽然借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但此时作品里呈现的物象已远非原本意义上的客观物象,如此“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具有异曲同工的妙处。这与兆虬先生曾经涉猎油画,年画、版画、壁画、连环画等等各种画种,造型基础扎实,且速写功底极好不无关系,兆虬先生特别善于从速写的线条中提炼笔法,以结构与感受为框架,在重复、堆积、迭加中造成运动感;创作中多用大水大墨,变换丰富的墨色胜于直接用色彩来表现原本物象,作品中穿插的点与线,线和面没有明确的界限,纷杂而又感觉各有所属,而很少借用色彩渲染,依托水与墨的变幻静静地显露着清新飘逸的韵致,这也构成了兆虬先生“新现实”表现性水墨国画的基本架构。
兆虬先生的艺术主张远远不仅仅停留在框架结构上,在人物塑造上借助现代女性的口红、项链,牛仔短裙、休闲衣服上的英文字母等等意象符号,在当代社会嬗变为前卫、当下的文化指代,形成独特的意味。这些意象符号早已超越客观物象形而下的意义,成为一种文化心理与精神指向。挥洒传统的点线面色墨中,成为兆虬先生个人审美感受与体验,形成更经典、更具学术意味,使作品在灵动、洒脱的笔墨里体现出智慧与才情,也构成兆虬先生“新现实”表现性水墨艺术存在的独特而基本构成因素。
当下,大众低俗文化的传播和艺术市场的无序,对高雅艺术形成不小的冲击,致使徒有写实技巧而缺乏文化精神的写实艺术泛滥,从而使人们难以分辨现实主义的真正品格。兆虬先生对现实的人文关注和“新现实”表现性水墨画艺术的探索和实践而产生的突破性进展,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中国画继续前行的可能和希望。使我们感悟到国画自身的问题并不在画种、题材或材料本身,而在于驾驭它的人是否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觉和对这感觉的卓越表达。张伟
$ 


